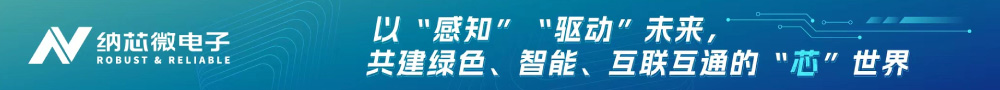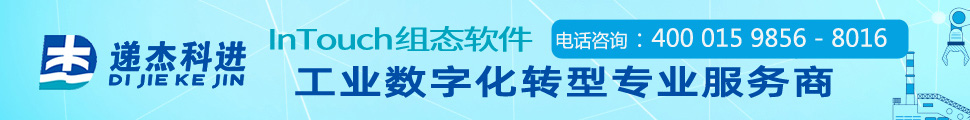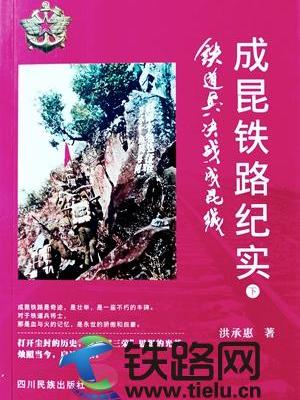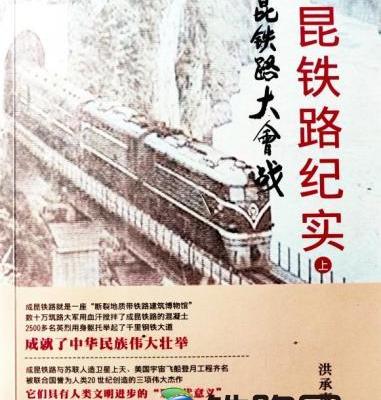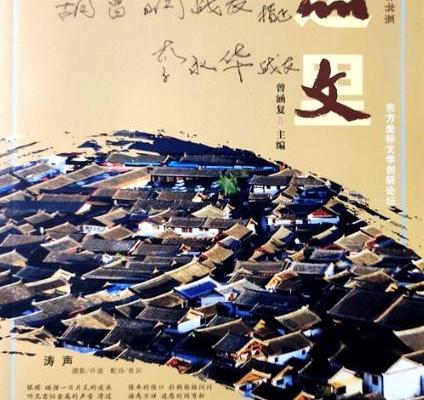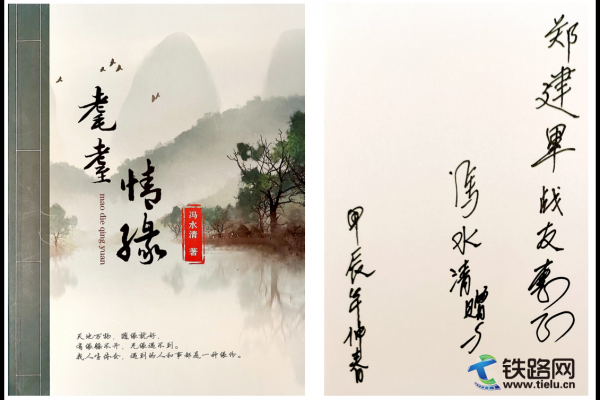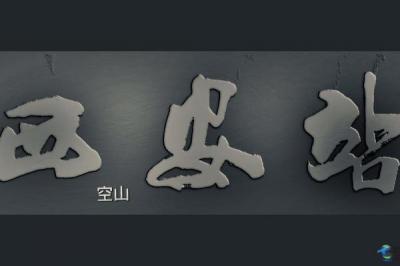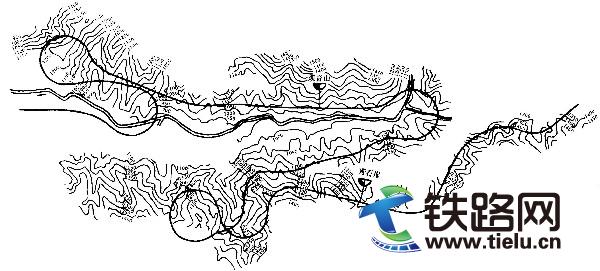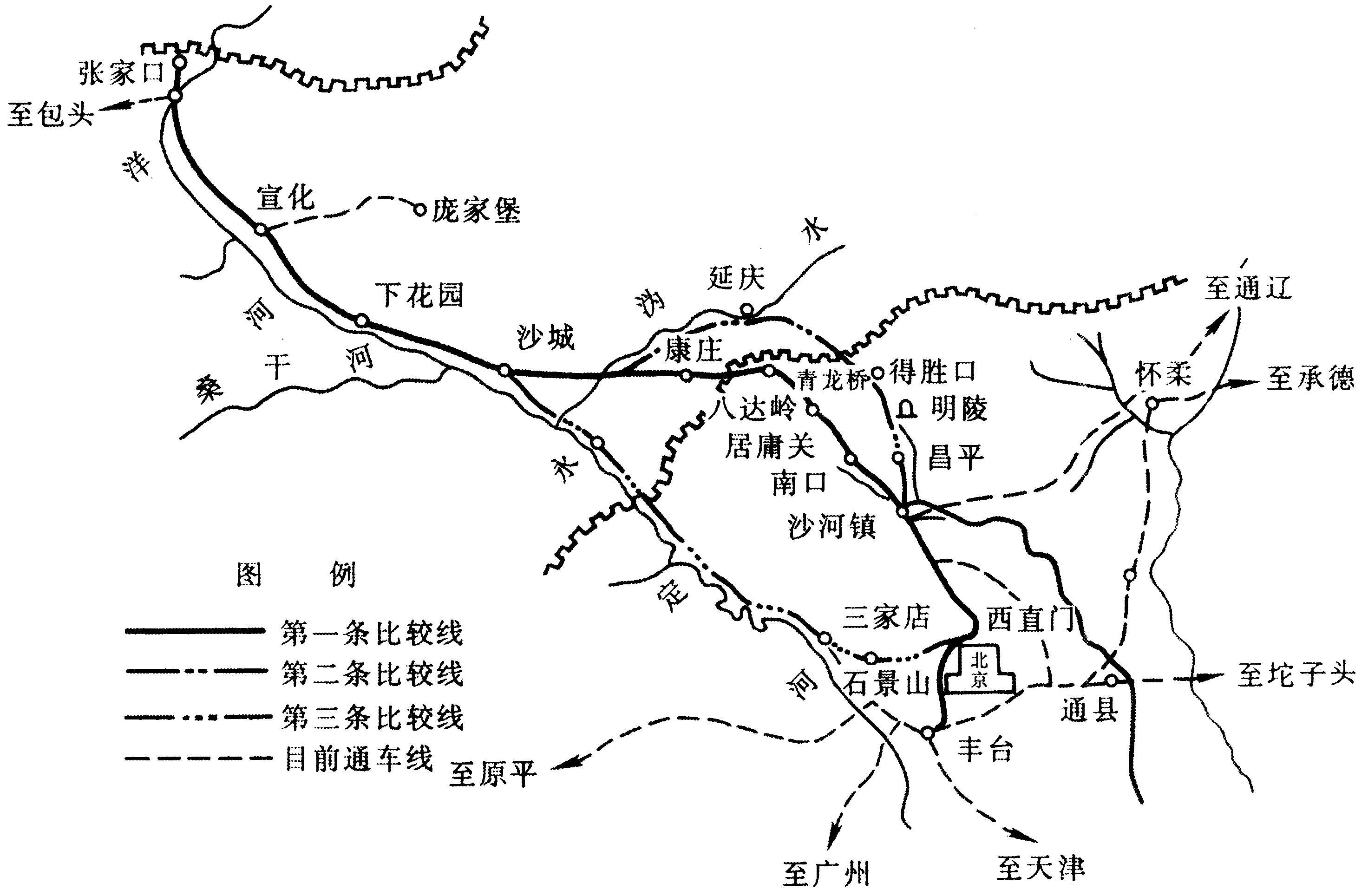鍵盤起落間編織出四十年春秋的經緯,銀絲偷渡鬢角時,我卻在字里行間觸到了永恒的春汛。寫作是種在骨血里的年輪,那些被月光沁透的深夜,那些與朝霞同醒的黎明,每個標點都是心跳的拓櫻從臨摹楷書的青澀,到草書般恣意的文風,文字終成生命的等高線,在時光褶皺里標記著精神的標高。
退休不過是換乘另一列文字專列。當青年作者們捧著初稿叩響房門,總看見四十年前那個在綠皮車上謄寫隨想的自己——軍用水壺壓著稿紙,列車搖晃的字跡里藏著整個時代的轍痕。如今在傳幫帶的月臺上,我把自己拆解成無數根枕木,鋪就往昔與未來的接軌處。王安石說"成如容易卻艱辛",寫作的犁鏵從來都是蘸著心血開刃。那些碰撞靈感的深夜,師徒圍坐宛若舊式信號燈下的編組場,將散落的文字車廂重組為駛向星海的列車。
鐵軌在晨霧中延伸的意象常令我出神。指導青工創作時,總在字句間聽見道釘夯入枕木的節奏。我們把安全規程寫成韻腳,將搶險故事釀成酒歌,讓鋼軌的震顫在段落間共振。當徒弟的散文登載《西南鐵道報》副刊,恍若目睹自己栽種的泡桐在站臺上開出紫色的瀑布。
暮色漸濃時,寫作反而成了破曉的儀式。教學筆記與創作手稿在案頭相互滲透,鍵盤敲擊聲里既有新苗拔節的脆響,也有老樁萌蘗的沉吟。那些被后輩文字點亮的時刻,像信號燈穿透迷霧,照見創作真正的奧義:傳承不是復印思想,而是點燃整片磷火帶。
四十年筆耕沉淀的,不過是半部未完成的站志。如今更愿做大山里那盞長明燈,目送南來北往的列車駛向我看不見的遠方。當他們的鳴笛聲穿透時代的雨幕,我知道,在時代的軌道上,文字永遠是最忠實的司鳴鐘。
免責聲明:本網站所刊載信息,不代表本站觀點。所轉載內容之原創性、真實性、完整性、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,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。